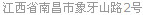张謇一生第四章落弟士人
时间:2025/4/10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 点击:
|
哪家白癜风医院便宜 https://m.39.net/disease/a_p3vdfaa.html四、落弟士人场屋蹉跌返乡备试张謇在吴长庆幕府先后十年之久,本想借助庆军建功立业,但是这个梦想随着吴长庆之死很快就破灭了,虽然不能说是壮志销磨,却颇有几分心灰意懒。嗣后,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托专人来延请他入幕,并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推荐请其聘用,都被张謇婉言谢辞了。正统儒家是讲究慎于出处的,张謇早就向友人说明过这层意思:“吾辈如处女,岂可不择媒妁,草草字人。”功名自然是需要的,但却不屑于“向纱帽下求生活。”这就是当年讲究操守的士大夫们的矜持。最后张謇带着七分懊悔与三分惆怅回到故乡,结束了他早年的游幕生涯。光绪十年()七月二十一日,张謇离开庆军幕府返抵家园。九月十四日《申报》传来了总督张树声病逝于粤军防次的噩耗。张树声与吴长庆一样,都是张謇非常敬重的爱国将领。张謇认为他们的相继死亡,归因于李鸿章的压抑和对国事的忧愤。因此他更有感于政海波涛的险恶,心情愈加抑郁。就在这一年,周边的局势十分的紧张,中法战争爆发,朝鲜又发生“甲申政变”,中国东北与南部边陲的局势也趋于紧张。这时的张謇对形势虽然还很关心,但多限于在信函中发表一些空泛的主战言论,并没有多少积极的具体建议,甚至对友人还流露出消极的情绪。如在致朝鲜参判金允植函,在谈到辞谢张之洞等督府礼聘时自我表白:“自以天下之事,方用纷纷,好伪惧真,所在而是。苟非难进而易退,鲜有平丧身而辱名者,是用卷然,引义避谢。”可见他过于珍惜个人的声名,为保全个人名誉,甚至在国事危急之际,仍然主张“难进而易退”,这正是封建士大夫标榜道义所隐藏的弱点。不过张謇经过长期的游幕历练,加以一贯勤奋读书,在学识和干才两个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。特别是赴朝以后,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都积累了经验,这更使他超越一般的科举士人,逐步侪身当代名士的行列。但是张謇在思想上却难以超越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格局,一直把科举视为“正途”,他囿于考道,遵从父命。在回家的十多年间,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场屋蹉跌,成为一名落弟士人。19世纪末,人们仍然习惯于把科举视为“正途”,所以张謇很难超越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惰性影响。张謇回乡以后,至少是囿于孝道,遵从父兄之命,在10年间一次又一次经历了场屋的蹉跌。早在光绪五年()五月,张謇曾回通州参加过优行试,被主考官吏部侍郎夏同善录取为第一名(亦称贡元)。同年七月底,张謇在江宁参加两江总督沈葆桢、巡抚吴元炳、学使夏同善对优行生的会考,亦被取为第一名。贡生有恩贡、岁贡、拔贡、优贡、副贡之别,张謇属于文品均的优贡。贡生比廪膳生稍高一个层次,如定制一般生员品服式只能用银顶,而贡生可用金顶。此后几年,由于母丧和“壬午之役”事忙,张謇未能再次参加乡试。直到光绪十一年()四月,张謇由上海乘船北上京师,参加顺天乡试。此时张謇由于国事家事都不如人意,心情颇为抑郁,这使他内心又增加了几分沉重。幸好到北京以后得到张裕钊、文廷式、袁昶等师友的关切与鼓励,才又安下心来认真作乡试准备。六月十一日循例在国子监“考到”,经祭酒盛昱录取为第一名,多少受一些鼓励。八月八日入考场,文、沈、王旭庄、梁鼎芬等新知旧好友均来“送场”,鼎芬且增送食物,这都是为了鼓舞张謇的斗志。清朝乡试分三场,八月初九为首场正场,十二日为二场正场,十五日为三场正场。首场题出于四书(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),二场题出于五经(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《礼记》),三场则为策问五道,涉及经史、时务、政治等方面。张謇自幼至长,历经十多年岁、院、科、乡各级考试的反复锻炼,已经学会了应付科举考场的全副本领。撰写八股文章自然是熟能生巧,所以善于利用其基本构架与逻辑规范,隐约地“自道其心之所明,自见面目”。这是一种颇有趣味而又相当艰难的游戏,好比是足球比赛的合理碰撞,或是乒乓比赛的擦边球,只有体育高手才能得心应手。张謇已是多经场屋蹉跌之人,尽管有人索稿纷如,赞誉备至,他仍无必中把握。八月十九日,也就是三场结束后的第二天,张謇以卷稿请张裕钊审阅,老师“甚见许可”,友人亦置酒慰问。但张謇仍不免在关庙求签,结果求得“四十签上吉”,签文是:“新来换得好规模,何用随他步与趋。只听耳边消息到,崎岖立局见亨衢。”仿佛正是冲着张謇报来的佳音。九月十一日乡试发榜,张謇以第二名被录取。据说有清一代南方士人取中“北榜”(指顺天乡试)第二名的并不多见。从顺治十一年()到光绪十一年(),先后年中,只有顺治甲午科盛于亮,乾隆庚午科方汝谦,光绪乙酉科张謇,一共仅有三人。“物以稀为贵”,他们虽然不是“会元”,却习惯称作“南元”,就是参加顺天乡试的南方士人中的魁首。张謇自从十六岁考中秀才,先后经过17年断断续续的试场折磨,直到三十三岁才取中举人,而且又是引人注目的“南元”,心里当然十分高兴,但是,张謇的科举之路并非从此一帆风顺。光绪十一年张謇32岁,高中顺天乡试第二名“南元”。图为张謇应试的“硃卷”张謇自从同治七年()到光绪十八年()先后25年中,历经县、州、院、乡、会等各级考试20多次,其中直接消磨在考场上的时间,就是多天,科举应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,不能不使张謇灰心丧气,并且已经对空洞陈腐的八股制艺感到厌倦。他曾这样追述:“应试之求屡进而亦渐悟虽应制诗文,亦当自道其心所明,自见面目,不戾于凡为文之义理。三十三试顺天,中式举人,自信益坚。顾试礼部又四槟,年四十矣。私以为私于有司供其喜怒而寒燠者,已二十六年,可已矣。”张謇确已心灰意懒,对科举失去了信心,因此,连常用的那套考具也扔掉了。屡试不中名落孙山张謇在中举以后,于光绪十二年()、十五年()、十六年()、十八年(),先后四次参加礼部会试,结果都是名落孙山。张謇在考场上虽然屡遭挫折,但却正是在这些岁月里,与南派清流迅速结合起来,从而获得了另一种进取的机缘,并且终于使他进一步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。张謇与南派清流的初步接触,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末,而最重要的结果,则是他开始得到当时全国知名度极高的若干大人物的赏识。其中尤以翁同龢关系最好、最密切。南派清流发现张謇这个人物并加以扶植,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。翁同龢的家乡常熟与南通隔江相望,由于地缘的关系,翁同龢很早就把张謇作为乡里的后起之秀加以奖掖。这一点可以从张謇多年以后写的《奉呈常熟尚书》的诗中得以证明。诗中所谓“十年辽海军”指在庆军客幕期间,翁同龢致吴长庆函时,经常附笔问候张謇。翁同龢像光绪十一年()春夏之交,张謇到京师参加顺天乡试,又结识了黄绍箕、王仁堪、梁鼎芬、沈曾植、盛昱、澲子潼、张云官、丁立钧、王松蔚等,这些人都是翁、潘门下的清流名士。张謇乡试高中,更使清流们感到欣慰。张謇在他的自订年谱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况和感受。他写道:“九月十一日,听录,中第二。潘、翁二师期许甚至,翁尚书先见余优贡试卷,试前知余寓距其宅不远,访余于庙(张謇住在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文昌关帝庙),余一答谢。”“潘师命为《乡试录前序》,翁师命为《后序》。”从此张謇与翁、潘正式形成师生关系,与清流的结合又进了一层。清流派非常重视自己的“正途”出身和翰林清望,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这个后起之秀尽快走完科举的漫长路程,及早正式加入到自己的行列中来。因此从光绪十二年()以后,他们利用手头有限的主考录取权力,曾经四次暗中模索,并动了手脚,总希望帮助张謇取中进士,但是都未能如愿,且误中他人,面对这种李带桃僵的结局,张謇只得自叹命乖,甚至尽弃试具,不再作功名之想。这自然又使清流派们多少感到有些沮丧。光绪十二年()三月举行会试,典试者为吏部尚书锡珍、左都御史祁世长、户部侍郎嵩申、工部侍郎孙毓汶。他们对这个新科“南元”的应试,似乎没有表现出特殊的
|
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
http://www.lsmzo.com/zlyy/14472.html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